电影《米花之味》是一部获得不少赞誉的文艺片。电影讲述了返乡青年在云南边境傣族村寨的家,如何与自己的女儿从隔膜、对立走向相互理解、和谐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,电影主创植入了许多现实主义的乡村问题思考,也以一种不乏愉悦、平静又略带幽默的语调表达了诸如乡村与城市、传统与现代的哲学命题。
影片中,这个年轻的母亲开着一辆人货两用车从上海回到家乡时,天色已暗。她开始以“外来者”的目光,饶有兴味地观察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寨,感受到故乡在外界冲击下的诸多变化。她最关注的对象是她的女儿 —— 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。正像媒体报道过的一些农村留守儿童一样,女儿也沾染上了一些不良生活习气,如撒谎、染上网瘾、厌学、小偷小摸等。这使作为母亲的她十分焦虑,影片的叙事在主要矛盾爆发时很有点“还乡体日记”风格。
主人公在试图矫正女儿行为的过程中,显现出她作为一个“外来者”的心态和思想,无形中受到故乡村寨文化的影响。家乡如画的景色、缅寺里的氛围,让她心神宁静。她甚至在这段时间内,找寻并发现了自己在精神上可皈依的文化本性。这部电影中,主人公的感情表达是复杂的: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影响下的物是人非,在家乡仿佛事事不尽如人意;另一方面,家乡以她特有的方式慰藉并悄然改变着自己。
因此,观众在电影潜在的结构里可以看到两种力量的较量:一种力量里,事件频发,冲突剧烈;另一种力量里,温柔博大,润物无声。这种复杂的书写故乡的方式,实际上来源于“现代都市人”的某种身份困惑或自觉。在这里,主人公返乡的“前史”很重要,她从大城市上海回来。而上海与家乡处于文化的两端,这决定了她凝视家乡的视角与视野,并进而窥测到它的“皮与里”。
主人公在上海的职业经历没有丝毫透露,但她在回乡之前,显然已经阅尽世间百态,经历过一番心理挣扎。而乡村的种种混乱最终没有击倒主人公,反而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自足,满足了她作为现代人的乡愁。
主人公以一个温和、知性的女性形象示人,但她作为叙事者、聚焦者、发现者的身份意识一直很强大。这个傣族村寨,成了主人公精神的演练场。她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观察、体验、细节描述颇具社会学家的眼光。孩子们在缅寺门口“蹭wifi”的情景、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与捐赠场景等,都再现得十分有力。女儿的好友、一个留守儿童,患了红斑狼疮,这个免疫力低下的疾病在“返乡体”的书写里,应当有对乡村命运的隐喻内涵。村寨的主事者没有送病人去医院,却请来了“山神”,结果因为耽误治疗,女孩在父母赶回来不久后便不治身亡。村寨为此疾病启动的应急措施尽收主人公眼底,但她却没有实质性的干预,甚至在那个神神叨叨的“山神”作法结束后指向虚拟的“白马”时,路过的她也俏皮地配合表演,绕路走开。
作为叙事聚焦者,主人公的眼里总会发现传统与现代的两种物象并列呈现,但并不见这些符号之间发生冲突。这种符号的糅杂在主人公眼里似乎早已经司空见惯。全寨村民穿上盛装去拜石佛时,石佛的大门上挂着“今日休息”的牌子。村民穿墙而入并开始舞蹈时,湛蓝天空掠过一架飞机。这样的描绘也尽显影片主创对村寨传统文化的态度,而主人公作为旁观者,她似乎尊重整个村寨的文化生态。自从进入村寨后,她逐渐习惯穿传统民族服装,逐渐与环境融为一体。
影片中还有一个“社工”的形象。除传统文化之外,这是主人公在村寨中观察到的一个具有现代生活意味的代表性形象。不过,这个人物仍旧是“民间权威”的形象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整个村寨的权威系统屏蔽了时政框架的影响,这也体现出作为“现代人”的主人公的视野局限。对真正现实权威形象的疏离,使得影片缺少了真正现实主义的描绘,也可见这个边境村寨的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想象,这也决定了电影呈现矛盾的方式及最后主人公“走向内心”的精神出路。对乡民的愚昧不放大,不推向冲突境地,傣寨的美好风景成为柔化村寨矛盾的主要手段。以乡村出路为引子,影片最后落实到了现代人精神出路的层面。乡村虽有残缺,仍旧是尽在咫尺的治愈之道,而现代人的出路却需要反躬自省。
电影的结尾暖心治愈,甚至可以读出禅意。主人公与女儿离开乡民,来到山洞的石佛面前,发现洞里的奇异声响来自一只钟乳石滴水下的易拉罐。母女俩在无声源音乐的伴奏下翩然合舞,瞬间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合无间,也想象性地解决和治愈了所有的身份差异及其精神焦虑。
本部影片部分主创来自于台湾的蔡明亮团队,观众可以很自然地体会出这种文化表述的精神来源与台湾式“小清新”的关系。主人公的旷达和优雅终究缺乏依据,她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的心理重建和精神系统恢复的过程,貌似有几分玄妙,其实也有些苍白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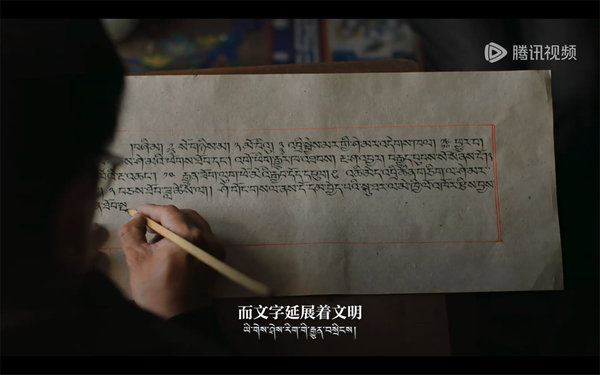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7870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7870号